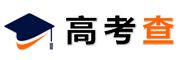摘 要:白居易的文化人格具有二重性: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与独善其身的人格追求交织在一起。白居易由早年积极进取的精神逐渐遁入个人生活,其思想由儒家转向佛老。故其文学品格既有意激刚健的一面又有闲适淡泊的一面。其文化人格继承了中国传统知识人关怀天下与追求独立人格的文化传统。中唐时期传统社会形态的转型,士人审美情趣与社会意趣的转型是其文化人格二重性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白居易 文化人格 文学品格
一
白居易《与元九书》曰:“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可谓是白居易一生的写照。他早年积极上疏,写下七十五篇“对策”,并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作。其为人刚正不阿,敢于直言。唐宪宗对其直言犯上颇为不满,谓李绛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绛对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诛,事无巨细必言者,盖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轻言也。陛下欲开谏诤之路,不宜阻居易言。”[1](P4344)通过二人的对话足见白居易敢于直谏,不避刀斧,以天下为己任。
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坠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置彼周行”,[1](P4344)受此诬陷被贬江州司马。
白居易切身感受官场的明争暗斗和世情冷暖后,逐渐转向佛道思想,“居易儒学之外,尤通释典,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在溢城,立隐舍于庐山遗爱寺,尝与人书言之曰:‘予去年秋始游庐山,到东西二林间香炉峰下,见云木泉石,胜绝第一。爱不能舍,因立草堂。前有乔松十数株,修竹千余竿,青萝为墙援,白石为桥道,流水周于舍下,飞泉落于檐间,红榴白莲,罗生池砌。”[1](P4345)
白居易中年以后,逐渐从政治生活走向个人日常生活和心灵世界。在苏州、杭州刺史任职期间,流连于江南的美好风光,写下了《钱塘江春行》等千古流传的诗篇;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其“和陶诗”政治激情已经淡去,悠远平和,宁静淡泊。白居易作诗以自表,其晚年诗作《醉吟先生传》曰:“凡观、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人家有美酒鸣琴者,靡不过;有图书歌舞者,靡不观。”[2]从中可以窥见白居易晚年生活,流连于山水、歌舞之?。
白居易的人生态度和自我追求,在其感伤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其感伤诗既有对现实的感发,也有对自我命运的哀叹,“事务牵於外,情性动於内,随感遇而形於叹咏”,融合了白居易诗歌创作的两个方面。《琵琶行》可见白居易由积极进取转向隐世避世的心路历程。人生坎坷,心中苦闷无处诉说。琵琶女发之为声,白居易则发之为文,“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尝尽世间辛酸,看尽世间沧桑,白居易由现实功名转向日常生活和心灵世界,沉醉于花前月下的个人生活,“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
其文化人格的二重性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特别是文人的共性特点。孔子周游列国积极入仕,“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终生不遇,退而论《诗》《书》,著《春秋》。司马迁忠心事主,而受宫刑,著《太史公书》以明志。杜甫心存天下,却颠沛流离,不受重用,写诗以抒心中之愤。蒲松龄,受尽科举之苦终生不第,退而成孤愤之书以寄托心中愤懑之情。
文化人格决定文学品格,白居易文化人格的风格的二重性,决定了其文学风格的多样性。
白居易把自己的诗歌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在《与元九书》曰:
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於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务牵於外,情性动於内,随感遇而形於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短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四百馀首,谓之“杂律诗”。
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一方面继承了儒家的诗教观,“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补察时政,抨击社会现实;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其诗作《卖炭翁》《买花》等“新乐府”诗作通俗而暗寓讥讽,践行了他志在兼济的人生理想和诗歌主张。在白居易的诗歌理论里,诗可以“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另一方面转身日常生活,吟咏情性,其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其闲适诗“知足保和,吟玩情性”。其讽喻诗、闲适诗,都有尚实、尚俗的风格。但是讽喻诗写得刚健意激、浅易直白,反映民生疾苦;其闲适诗,“皆寄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游乐不暇”;其风格淡泊、闲逸、平和,含蓄蕴藉,充满生活情趣。
白居易的文化人格前期以“兼济天下”为根本特征,故其讽喻诗写得出彩,审美性与实用性兼备;中晚年的文化人格以“独善其身”为根本特征,故其闲适诗、和陶诗写得自然,有韵味。
二
其文化人格的二重性与思想的多元性,决定其文学风格的多样性。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中唐文人文化人格的二重性,有其特殊的现实原因和文化传统。
其一,隋唐以来,门阀士族地主的政治垄断地位渐渐被打破,特别是科举取士为庶族地主打开一扇入仕之门。初唐四杰英俊沉下伦的呐喊,“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他们要求参与政治。中唐上层统治者力主改革,科举取士大大增加,庶族地主逐渐参与国家政治,“作为庶族文人的杰出代表,元白的参政意识与仕宦热情尤为积极而强烈,政治目标也更为具体而现实”[3](P263)。白居易、元稹、大历十才子、韦应物、韩愈、柳宗元都以庶族身份进入上层政治。另一方面,庶族地主失去背后强大家族的支撑,其地位并不稳固。庶族地主无力左右朝政,因而中央集权加强,君主的权力增强。庶族地主的仕途,或因党争,或因触犯上层利益,而仕宦颠沛不定。故文人对人生沉浮感受尤为明显,仕途的打击,人生理想的破灭,对人情冷暖的重新认知,都使他们转向心灵的书写和愤懑之情的抒发。白居易的讽喻诗对现实政治的关怀,闲适诗对日常生活的吟咏,实际上反映了仕途受挫前后截然不同的心态。中唐朝政,自长庆以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文人集团失去了在政治上的话语权,白居易逐渐淡漠、逃避政治,“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即多忧患。帷有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其二,中国士人自其诞生起就抱持“以道易天下”的宗教救世情怀。孔子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4](P109)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旨》一文中谈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5](P3289)司马迁论《春秋》曰:“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顾炎武曰:“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6]白居易担负一种救世补正的责任与意识积极从政,希望以自己的政治理念即心中的“道”来改造社会。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中国传统精神儒道互补。“表面看来,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实际上它们刚好相互补充而协调。不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经常是后世士人的互补人生路途,而且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也成为中国历代士人的常规心理”[7](P32)。从古至今中国传统社会经历了多次文化整合,士人们形成了一种相互平衡调剂的双重人格??儒道互补之双重人格。
其三,中唐是中国审美意识形态转型的一个时期,庶族地主和市民阶层的审美品位逐渐代替了门阀士族高雅的美学追求和形而上的哲学追求。他们更关注现实,更实际。这一时期,仕进途径由塞外战功逐渐转向诗赋取士,故士人作诗赋以谒进,追求华章和辞藻的华美,追求安乐、奢华的生活成为这一时期社会上层的共同倾向,“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绘画,或侈于博弈,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这一时期的文人,我们发现,与白居易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的元稹,其悼亡诗写的尤为出彩。通过他的悼亡诗足见丧妻对其人生的巨大打击,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其人生兴趣已经转向个人生活。韩愈倡导古文运动宣扬道统和儒家思想;其文章嘲讽现实、嬉笑怒骂,表现出对现实强烈的干预精神;与之相对立的是韩诗遁入心灵世界的抒发;韩愈在个人生活方面追求高官厚禄,奢靡的生活。柳宗元的诗冷峭简淡,现实的悲愤与怨艾充斥其间;与之相对的是其山水游记优美、宁静、淡远。这一时期的时代精神由人生的功业转向了个人日常生活和心境。正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所言“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7](P32)白居易、元稹、韩愈、柳宗元等中唐文人逐渐淡去对政治的热情,转向对个人家庭生活、个人心境、人生意趣的抒发。故孟郊、李贺、李商隐诗歌转向人的心境的抒写,宋词逐渐转向对个人愁绪等心境的描摹。
总之,白居易为代表的中唐文人文化人格的二重性,蕴含着一个内在趋势,由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由社会转向日常生活,由事功?向心境、意趣。其内在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的审美情趣、人生意趣逐渐改变。秦汉的社会审美、魏晋的自然审美转向心境的审美,后来宋词对意境特别是心境的把握、宋明理学特别是王阳明心学的产生足以为证。
注释:
[1][后晋]刘?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2][唐]白居易撰:《白氏长庆集卷六十一》,四部?刊景日本翻宋大字本。
[3]许总:《唐诗史(下)》,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4]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
[5]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6]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五》,四部?刊景清康熙本。
[7]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参考文献:
[1]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