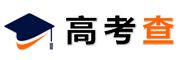《中国诗与中国画》读后感
在我手头的这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钱锺书散文》里,《中国诗与中国画》是《七缀集》的第一篇。这篇文章到底作于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但从我手里这部散文集里作品的排列顺序,给我的感觉是,这篇文章好像是钱锺书文章前后期的一个分界。就这部《钱锺书散文》里的文章来说,都具有钱锺书写作时候体现出的机灵、幽默的特点,尤其善用巧妙地比喻来明、刺现实生活中的情况。亚里士多德说:善用比喻是天分高的表现。钱锺书在文史哲一类的读书、写作上确实有一股天生的机灵气,只是在前面的一些文章中这种机灵体现的更多一点。例如《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窗》、《论快乐》等等,让我读起来,感觉和写作《围城》的那个钱锺书很接近。估计这些文章和《围城》的写作年代也差不多,都是钱锺书早期的作品。这些早期的作品,我感觉,更像是典型的散文,篇幅都不是很长,引经据典的现象不是很多,主要是自己主观意识的发挥,随处可见他的那种机灵幽默,读起来很轻松。而之后的文章,文学韵味越来越少,学术气质越来越强。钱锺书的文笔,他的旧体诗暂且不论,就说他在小说、散文中的文笔,是偏于瘦、硬的,没什么肥词腴句,但就连这么一点文学韵味也在逐渐减少。越往后的文章关注的问题越学术化,写作方式中的引经据典的现象比比皆是,真有掉书袋的味道,仿佛他的思想由文学的阔而漫转变为学术的精而专,形成的每一种观念都不是单纯凭自己的主观意愿而要有充足的理论依据,写下的每一笔都不再像文学写作那样随意挥洒而要引经据典的笔笔皆有根据,文章的篇幅从总体来讲都增大了,读起来感觉沉甸甸的,好像说一点就是确凿的一点。直到《七缀集》的第一篇《中国诗与中国画》,基本形成了在《管锥编》中可以见到的写作风格,虽然《七缀集》的文章都是用白话文写成,但神理一致。所以,他后来的文章如果再叫做散文,我真感觉有点不准确了。我总以为,散文更多的属于文学范畴,用散文来称呼《七缀集》的文章,从文学魅力来讲,美化了它们,从思想理论来讲,委屈了它们。或许我对散文这个概念的外延在理解上有局限,现在不是有很多所谓的文化散文、学术散文么,例如余秋雨之辈的作品,我认为,那只是伪学者跑到散文中来装腔作势。我对钱锺书还是尊敬的,不能用这种不伦不类的名称来称呼他的文章,姑且称为论文吧。
杨绛先生在为《管锥编》做的代序中写到,钱锺书称他早年的作品是“小时候干的营生”,现在看来会使他“骇且笑”,认为那是他成长过程的表现。这说明钱锺书确实有一个由文学者成长为文史哲学者的过程。他曾是个作家,但他并没有停留在作家的身份上,更进一步成为了学者。
就我读《中国诗与中国画》,本人业余读书人一个,就不进行什么学术探讨了,只说点个人想法。这篇文章确实符合“管锥之义”。一管窥去、一锥刺下,虽小虽微,但是确凿的一点一星。《中》文里,长篇大论的引经据典,这是《七缀集》里文章的共同特点,钱锺书丰富的学识、谨慎的治学态度由此体现,但也由此受到一些人的诟病。说实话,这样掉书袋的风格真不是十全十美,《诗可以怨》我就耐着性子读下来的,无论如何不欣赏。但在这里我还是理解并叹赏的。《中》文的核心意旨很明白,就像文末一段总结的,对历史上的泛泛的诗画并举的论调做了精辟的指摘,确凿的指出具有南宗画风的诗、也就是神韵派诗风的诗不是中国诗中的高品、正宗,相当于神韵派诗风的画、也就是南宗画却是中国画中的高品、正宗。那么长的篇幅,那么多的引经据典,就为了这个观点的明确。我看到这里,当时就有个感觉,至于吗?中国画我不知道那么多,要说中国诗,王维的诗明显比李白、杜甫差一个级别,因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嘛,再因为……这古往今来的人不都是这么说么。惭愧,这正是又一种泛泛之论啊。钱锺书先生在此花如许的精力论证出这么一点确凿,管窥锥刺,虽小却实,后来人若能据此作出国学上的新学问,此文当有基石之功。《中国诗与中国画》,洋洋万言、广征博引,产下一个单纯的常识。文章真如一块砖、一块石,坦坦实实的摆在那里。有一些人,或者真的具有高蹈绝伦的却又暂未表现出来的才学志向,或者就是低劣的哗众取宠,指摘钱锺书的学识文章。我真想对他们说一句,您先做点这样的硬功夫再说吧。
在我手头的这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钱锺书散文》里,《中国诗与中国画》是《七缀集》的第一篇。这篇文章到底作于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但从我手里这部散文集里作品的排列顺序,给我的感觉是,这篇文章好像是钱锺书文章前后期的一个分界。就这部《钱锺书散文》里的文章来说,都具有钱锺书写作时候体现出的机灵、幽默的特点,尤其善用巧妙地比喻来明、刺现实生活中的情况。亚里士多德说:善用比喻是天分高的表现。钱锺书在文史哲一类的读书、写作上确实有一股天生的机灵气,只是在前面的一些文章中这种机灵体现的更多一点。例如《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窗》、《论快乐》等等,让我读起来,感觉和写作《围城》的那个钱锺书很接近。估计这些文章和《围城》的写作年代也差不多,都是钱锺书早期的作品。这些早期的作品,我感觉,更像是典型的散文,篇幅都不是很长,引经据典的现象不是很多,主要是自己主观意识的发挥,随处可见他的那种机灵幽默,读起来很轻松。而之后的文章,文学韵味越来越少,学术气质越来越强。钱锺书的文笔,他的旧体诗暂且不论,就说他在小说、散文中的文笔,是偏于瘦、硬的,没什么肥词腴句,但就连这么一点文学韵味也在逐渐减少。越往后的文章关注的问题越学术化,写作方式中的引经据典的现象比比皆是,真有掉书袋的味道,仿佛他的思想由文学的阔而漫转变为学术的精而专,形成的每一种观念都不是单纯凭自己的主观意愿而要有充足的理论依据,写下的每一笔都不再像文学写作那样随意挥洒而要引经据典的笔笔皆有根据,文章的篇幅从总体来讲都增大了,读起来感觉沉甸甸的,好像说一点就是确凿的一点。直到《七缀集》的第一篇《中国诗与中国画》,基本形成了在《管锥编》中可以见到的写作风格,虽然《七缀集》的文章都是用白话文写成,但神理一致。所以,他后来的文章如果再叫做散文,我真感觉有点不准确了。我总以为,散文更多的属于文学范畴,用散文来称呼《七缀集》的文章,从文学魅力来讲,美化了它们,从思想理论来讲,委屈了它们。或许我对散文这个概念的外延在理解上有局限,现在不是有很多所谓的文化散文、学术散文么,例如余秋雨之辈的作品,我认为,那只是伪学者跑到散文中来装腔作势。我对钱锺书还是尊敬的,不能用这种不伦不类的名称来称呼他的文章,姑且称为论文吧。
杨绛先生在为《管锥编》做的代序中写到,钱锺书称他早年的作品是“小时候干的营生”,现在看来会使他“骇且笑”,认为那是他成长过程的表现。这说明钱锺书确实有一个由文学者成长为文史哲学者的过程。他曾是个作家,但他并没有停留在作家的身份上,更进一步成为了学者。
就我读《中国诗与中国画》,本人业余读书人一个,就不进行什么学术探讨了,只说点个人想法。这篇文章确实符合“管锥之义”。一管窥去、一锥刺下,虽小虽微,但是确凿的一点一星。《中》文里,长篇大论的引经据典,这是《七缀集》里文章的共同特点,钱锺书丰富的学识、谨慎的治学态度由此体现,但也由此受到一些人的诟病。说实话,这样掉书袋的风格真不是十全十美,《诗可以怨》我就耐着性子读下来的,无论如何不欣赏。但在这里我还是理解并叹赏的。《中》文的核心意旨很明白,就像文末一段总结的,对历史上的泛泛的诗画并举的论调做了精辟的指摘,确凿的指出具有南宗画风的诗、也就是神韵派诗风的诗不是中国诗中的高品、正宗,相当于神韵派诗风的画、也就是南宗画却是中国画中的高品、正宗。那么长的篇幅,那么多的引经据典,就为了这个观点的明确。我看到这里,当时就有个感觉,至于吗?中国画我不知道那么多,要说中国诗,王维的诗明显比李白、杜甫差一个级别,因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嘛,再因为……这古往今来的人不都是这么说么。惭愧,这正是又一种泛泛之论啊。钱锺书先生在此花如许的精力论证出这么一点确凿,管窥锥刺,虽小却实,后来人若能据此作出国学上的新学问,此文当有基石之功。《中国诗与中国画》,洋洋万言、广征博引,产下一个单纯的常识。文章真如一块砖、一块石,坦坦实实的摆在那里。有一些人,或者真的具有高蹈绝伦的却又暂未表现出来的才学志向,或者就是低劣的哗众取宠,指摘钱锺书的学识文章。我真想对他们说一句,您先做点这样的硬功夫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