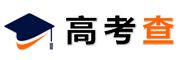两个故宫的离合读书笔记
“北京故宫胜在量,台北故宫胜在质。”这样的论断早在读《两个故宫的离合》前就听过。国民党在大陆解放前夕挑出最珍贵的故宫文物偷偷运往台湾不仅仅作为国民党注定败北的事实被谈起,更是作为国民党破坏国家统一的罪证被批判。“翠玉白菜”、“肉形石”和《清明上河图》??作为那批珍贵文物的代表它们被多少爱国人士魂牵梦绕。而对年轻人来说,台北故宫的魅力则更多地来自它不拘一格和诙谐的一面:7月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印有康熙朱笔御批“朕知道了”的胶带,迅速成为微博上的热门话题。政治博弈和流行文化就这样交织在人们对台北故宫的揣测和想象中,而北京故宫则是度量台北故宫的尺度,述说着圆满和残缺,分离和重聚,过去和现在。
也许,由一个局外人来书写这两个故宫的历史是才是最不偏不倚、最合适的。
班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任何一个现代民族都是想象的、有明确界限的、且拥有主权的政治共同体(注一)。“想象”的成分在中华民族的构建中尤其突出。“孙中山为对抗西欧列强侵略中国,运用‘中华’的概念,将实际是多民族的中国人,整合成一个新国家的基础。所谓中华民族的人或民族,其实原本并不存在,这是为了定义革命所诞生的新共同体,而创造出来的政治概念”(野岛刚,29页)。虽为新共同体,中华民族的存在基础却是“旧”:在如今名为“中华”的这片土地上的波澜壮阔的历史与灿烂多姿的文化是消弥区域和阶级间隔,凝聚“中华民族”,应对西方文明强大冲击的关键所在。诚如野岛在书中所说:“在政治学上,权威是靠‘权力’和‘正统性’来确立的”(68页)。在古代中国,朝代更迭带来的是异姓皇室的统治,但唯一不变的是“天命”,而这作为中原文化系统被一代代传承下来;在现代中国,文化依旧是政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用来证明政治权力的道具,也是权力与社会、权力与历史的指标”(210页)。在中国人生活的各个层面都被西方文明全面侵蚀后,文化更是?卫民族尊严的最后底线。故宫集聚了华夏物质文化史的精华,是中国文化遗产的杰出代表,没有比这更能说明政权的“正统性”了。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的诞生,正因为此。野岛认为中华政治中文化的内涵与其他国家提倡的“文化重视”不同,对此我并不同意。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文化遗产都是构建民族历史和民族身份、维护“正统性”的重要工具。即使是拥有万世一系的天皇家族的日本,保护国家的过去亦是文化政策中十分重要的内容。例如,皇室陵墓一直得到各个政权的庇护,无论是过去以皇室私家领地的理由还是现在以文化遗产的理由。在中国,不过是因为大陆和台湾的对立更突出了文化蕴涵的权利斗争。
国民党和民进党围绕着台北故宫引发的一系列斗争更是耐人寻味,对于身处大陆的我们来说,亦非毫无关系。台北故宫的变迁,促使我们思考故宫和民众、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关系。
撇去狭隘的党派斗争不谈,前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杜正胜建立一个“以多元世界水平为目标的博物馆”的抱负实际上意义深远。中华二字含有的“璀璨世界文明中心”之意味,象征着中华文化中华夷思想这一基本概念。在故宫,这一价值预判表现为对中华物质文化史的单一、纯粹展示,这的确与其他世界闻名的博物馆(如巴黎的卢浮宫和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迥然不同。(www.gkcyc.com)在无法以世界文明中心自居的当下,中国如何证明中华文化之卓越?故宫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和骄傲,但是否能与其他举世闻名的博物馆相提并论?也许故宫不具备世界一流博物馆的实力是言过其实:毕竟以文化多元性来评价博物馆是西方国家在经历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掠夺后制定的标准,它未必适用于当今中国。我十分认同秦孝仪的观点:“多元化也许是世界博物馆的趋势,但一元的故宫以一元的华夏文化为特征,这是值得骄傲之处,不应视为弱点或负债”(43页)。我们应该从多元化趋势中学习的,也许应该是正视华夏文化自身的多元性:自古以来跨文化交流在中华物质文化史上留下了浓重的印记,我们应该承认“华”和“夷”的界限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泾渭分明,用任何一个单一的朝代来概括中华文明的特点亦有失偏颇。在重回文明大国的道路上,中国应该有这样的气度。
至于如何打通中华文化过去和现在的任督二脉,前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林曼丽提出的“Old Is New”值得学习:“为传统文物引进21世纪的技术,令其产生新的价值。各个文物都有其独特的背景和故事,应将文物的设计结合商品开发。文物艺术创作之初,也是运用当时最新的技术,因此今日的古典,其实是昨日的前卫。先进的技术从旧的东西得到养分,运用高科技可将人类遗产刻画入生活与心灵之中”。文物并不是死物,它们是经由时代浪潮拍打遗留在历史沙滩上的贝壳,镌刻着写满过去生活细节的年轮。它们亦为当下中国人的生活提供了无尽的素材,帮助我们重新定义何为中国人。主张与过去决裂的现代主义迄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它带来的虚无感促使了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既从传统中汲取养分,又不排斥现代主义的成果。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的文化、价值观被不断地并置与比较,那么我们该如何在这个日趋扁平的的世界中坚守中华文化的阵地?就故宫而言,走下国宝的“神坛”,拉近文物与生活的距离,或许是个不错的尝试。改为“依照年代顺序”来布置展品,亦有其可取之处:这让参观者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有更直观的了解。
历史和遗产有关联亦有区别:历史是对发生在过去的事实孜孜不倦的追求,尽管常常事与愿违,遗产是对历史事实的现代利用;历史避免偏见,遗产强调偏见;历史讲究精确,遗产讲究概括。为了建立与现实生活的联系,特别是当历史与人们的生活太过遥远时,历史化作遗产,让当下的人得以建立与祖先的联系(注二)。柯尼里斯?豪托夫(Cornelius Holtorf)在研究流行文化后发现,如今遗产与其说是历史教育不如说是当下叙事:“遗产叙述的故事部分是关于参观者自己:他们的社会背景、生活方式、集体身份、对其他历史时期的成见与幻想。”(注三)或许,从一开始遗产就是人们希望看到的、关于过去的表征而非过去的准确再现。而这希望看到的东西,随着不同人群的立场的改变而改变。那么,故宫是谁的故宫?它在述说着谁的故事?大陆和台湾的政权代表还是两岸民众?大陆人还是台湾人?中国人还是世界人?两个故宫的离合之间,不同的答案在被揭晓,被否定,被重构。
“北京故宫胜在量,台北故宫胜在质。”这样的论断早在读《两个故宫的离合》前就听过。国民党在大陆解放前夕挑出最珍贵的故宫文物偷偷运往台湾不仅仅作为国民党注定败北的事实被谈起,更是作为国民党破坏国家统一的罪证被批判。“翠玉白菜”、“肉形石”和《清明上河图》??作为那批珍贵文物的代表它们被多少爱国人士魂牵梦绕。而对年轻人来说,台北故宫的魅力则更多地来自它不拘一格和诙谐的一面:7月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印有康熙朱笔御批“朕知道了”的胶带,迅速成为微博上的热门话题。政治博弈和流行文化就这样交织在人们对台北故宫的揣测和想象中,而北京故宫则是度量台北故宫的尺度,述说着圆满和残缺,分离和重聚,过去和现在。
也许,由一个局外人来书写这两个故宫的历史是才是最不偏不倚、最合适的。
班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任何一个现代民族都是想象的、有明确界限的、且拥有主权的政治共同体(注一)。“想象”的成分在中华民族的构建中尤其突出。“孙中山为对抗西欧列强侵略中国,运用‘中华’的概念,将实际是多民族的中国人,整合成一个新国家的基础。所谓中华民族的人或民族,其实原本并不存在,这是为了定义革命所诞生的新共同体,而创造出来的政治概念”(野岛刚,29页)。虽为新共同体,中华民族的存在基础却是“旧”:在如今名为“中华”的这片土地上的波澜壮阔的历史与灿烂多姿的文化是消弥区域和阶级间隔,凝聚“中华民族”,应对西方文明强大冲击的关键所在。诚如野岛在书中所说:“在政治学上,权威是靠‘权力’和‘正统性’来确立的”(68页)。在古代中国,朝代更迭带来的是异姓皇室的统治,但唯一不变的是“天命”,而这作为中原文化系统被一代代传承下来;在现代中国,文化依旧是政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用来证明政治权力的道具,也是权力与社会、权力与历史的指标”(210页)。在中国人生活的各个层面都被西方文明全面侵蚀后,文化更是?卫民族尊严的最后底线。故宫集聚了华夏物质文化史的精华,是中国文化遗产的杰出代表,没有比这更能说明政权的“正统性”了。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的诞生,正因为此。野岛认为中华政治中文化的内涵与其他国家提倡的“文化重视”不同,对此我并不同意。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文化遗产都是构建民族历史和民族身份、维护“正统性”的重要工具。即使是拥有万世一系的天皇家族的日本,保护国家的过去亦是文化政策中十分重要的内容。例如,皇室陵墓一直得到各个政权的庇护,无论是过去以皇室私家领地的理由还是现在以文化遗产的理由。在中国,不过是因为大陆和台湾的对立更突出了文化蕴涵的权利斗争。
国民党和民进党围绕着台北故宫引发的一系列斗争更是耐人寻味,对于身处大陆的我们来说,亦非毫无关系。台北故宫的变迁,促使我们思考故宫和民众、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关系。
撇去狭隘的党派斗争不谈,前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杜正胜建立一个“以多元世界水平为目标的博物馆”的抱负实际上意义深远。中华二字含有的“璀璨世界文明中心”之意味,象征着中华文化中华夷思想这一基本概念。在故宫,这一价值预判表现为对中华物质文化史的单一、纯粹展示,这的确与其他世界闻名的博物馆(如巴黎的卢浮宫和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迥然不同。(www.gkcyc.com)在无法以世界文明中心自居的当下,中国如何证明中华文化之卓越?故宫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和骄傲,但是否能与其他举世闻名的博物馆相提并论?也许故宫不具备世界一流博物馆的实力是言过其实:毕竟以文化多元性来评价博物馆是西方国家在经历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掠夺后制定的标准,它未必适用于当今中国。我十分认同秦孝仪的观点:“多元化也许是世界博物馆的趋势,但一元的故宫以一元的华夏文化为特征,这是值得骄傲之处,不应视为弱点或负债”(43页)。我们应该从多元化趋势中学习的,也许应该是正视华夏文化自身的多元性:自古以来跨文化交流在中华物质文化史上留下了浓重的印记,我们应该承认“华”和“夷”的界限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泾渭分明,用任何一个单一的朝代来概括中华文明的特点亦有失偏颇。在重回文明大国的道路上,中国应该有这样的气度。
至于如何打通中华文化过去和现在的任督二脉,前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林曼丽提出的“Old Is New”值得学习:“为传统文物引进21世纪的技术,令其产生新的价值。各个文物都有其独特的背景和故事,应将文物的设计结合商品开发。文物艺术创作之初,也是运用当时最新的技术,因此今日的古典,其实是昨日的前卫。先进的技术从旧的东西得到养分,运用高科技可将人类遗产刻画入生活与心灵之中”。文物并不是死物,它们是经由时代浪潮拍打遗留在历史沙滩上的贝壳,镌刻着写满过去生活细节的年轮。它们亦为当下中国人的生活提供了无尽的素材,帮助我们重新定义何为中国人。主张与过去决裂的现代主义迄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它带来的虚无感促使了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既从传统中汲取养分,又不排斥现代主义的成果。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的文化、价值观被不断地并置与比较,那么我们该如何在这个日趋扁平的的世界中坚守中华文化的阵地?就故宫而言,走下国宝的“神坛”,拉近文物与生活的距离,或许是个不错的尝试。改为“依照年代顺序”来布置展品,亦有其可取之处:这让参观者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有更直观的了解。
历史和遗产有关联亦有区别:历史是对发生在过去的事实孜孜不倦的追求,尽管常常事与愿违,遗产是对历史事实的现代利用;历史避免偏见,遗产强调偏见;历史讲究精确,遗产讲究概括。为了建立与现实生活的联系,特别是当历史与人们的生活太过遥远时,历史化作遗产,让当下的人得以建立与祖先的联系(注二)。柯尼里斯?豪托夫(Cornelius Holtorf)在研究流行文化后发现,如今遗产与其说是历史教育不如说是当下叙事:“遗产叙述的故事部分是关于参观者自己:他们的社会背景、生活方式、集体身份、对其他历史时期的成见与幻想。”(注三)或许,从一开始遗产就是人们希望看到的、关于过去的表征而非过去的准确再现。而这希望看到的东西,随着不同人群的立场的改变而改变。那么,故宫是谁的故宫?它在述说着谁的故事?大陆和台湾的政权代表还是两岸民众?大陆人还是台湾人?中国人还是世界人?两个故宫的离合之间,不同的答案在被揭晓,被否定,被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