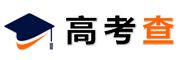繁华的北京周边环绕着河北省的25个国家级贫困县,235.9万贫困人口和最后一批隐居深山的村民。“十二五”规划打造的“首都经济圈”,将致力于消除这道刺眼的贫富沟壑。
原始的贫困,距离首都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在北京东北方向的燕山余脉深处,62岁的赵汉文和58岁的老伴一道,靠着5亩地相依为命。老人多年备受多种疾病煎熬,动过多次手术,老伴也一直没断药。当地很多村民认为他家应该至少获得一个低保资格,不过迄今仍没有。
这位河北承德市兴隆县蘑菇峪乡孙杖子村的村民,和全村数百人一道,祖辈隐居深山,刀耕火种,饮水靠打井和蓄山水,成为首都附近最后一批远离现代文明的人。这里的山道弯曲难行,汽车走完50公里路程需要5个小时,与150公里外的长安街反差强烈。
赵汉文所在的兴隆县,县城距北京市中心、工业城市唐山直线距离分别只有100公里左右,距河北省会石家庄有350多公里。向西接壤北京的平谷区。
上世纪90年代,兴隆曾是河北的小康县,经济实力与毗邻的北京平谷区不相上下。后来的十来年,平谷区日益发达,而兴隆则在今年年初首次被河北划为省级贫困县,与丰宁、围场、赤城等北京周边国家级贫困县为伍。
这些隶属河北省的贫困县围绕着富庶的国际大都市北京,形成了一个“环首都贫困带”。河北省发改委与河北省扶贫办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这一地带仍分布有25个国家级和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贫困人口235.9万人。
它们与北京市中心的直线距离大多在150公里以内。作为北京外围的水源和生态保护屏障,它们的经济发展受到制约。
由于多年来不被允许发展重化工业,不能种植耗水量大的水稻,不得放牧,这些环北京贫困县仍在艰难地寻求新的发展路径。如何填平北京身侧的这些刺眼的贫富沟壑,成为“十二五”规划所提出的“首都经济圈”面临的一个首要课题。
诊治“环首都贫困带”
最后的山里人
赵汉文一家住在燕山山脉余脉的三道沟东大甸子。从兴隆县城到蘑菇峪乡50公里的山路,汽车颠簸5个小时才到。
赵汉文从祖父一代都居住在这大山里。祖辈建在山上的住房抗战年代被日军烧毁。如今赵家住的房子,最新的一座已经住了20多年,是用泥土、红砖和石头等垒筑而成。过去房顶一直是茅草,直到近年才改为红瓦。
这些瓦块连同少量的红砖,都是靠骡子沿着崎岖难行的小路运进山来。小路是赵汉文和弟弟赵汉全开辟的,每次下雨都会被冲坏,再次下山就得再修理。上月21日北京那场灾难性的暴雨过后,现在这条路连骡马也不能走了。
赵汉文全家靠着5亩地过活,年收入5000多元。堂屋中央地上有一大锅,锅边的墙壁被熏得发黑。吃饭用的圆桌,红漆已经快要掉光。老旧的电视机还是早年的厚重机型。屋里唯一的新家具,是今年由当地电力公司赠送的一台豆浆机,
落后和贫穷使得村民纷纷迁离。姑娘们都出嫁到山下平原地区的家庭。小伙子选择倒插门走出大山。随着老年一代陆续故去,山上的居民越来越少。赵家所属的蘑菇峪乡孙杖子村11组,多年前山上曾住有100多村民,如今还有14户56人,但近年有一半的人搬走,留在山上的只剩30人左右,当中包括11组组长王立国,现年48岁,未婚。
赵汉文的闺女也已经嫁到邻近山脚有居住地的村子,儿子倒插门到平原地区居住的村。只剩下老两口仍住在山中。赵汉全住在他近旁,赡养着80多岁的老母亲和岳母。
西凹梁山还有3户人家,道沟梁山还有2户,北沟梁山上还有3户……这些最后的山里人也盼着下山。但村干部告诉他们,过去的下山搬迁指标主要给住在山上更偏僻地方的居民的,这些人全部搬走后,这几年再没有新的指标下达,因此难以解决剩下居民的下山问题。
赵汉全也认为,下山难度太大。“现在下山的,都是自己在山下买地盖房,这个需要花20多万,不是人人都有这个钱。而且山下现在也难找到闲置的宅基地了。”他说。
过去孙杖子村大山常年没有电,2006年当地电力部门栽了13个电线杆,花了30万元,为山里的村民们解决了供电。而当时这30万元,在山下盖房可以盖多套,赵汉全曾提议能否干脆把拉电的钱用来盖房和搬迁山民,电力部门答复:“修电线杆的钱必须专款专用。”
行政区划下的命运分野
首都身旁的贫富沟壑是怎样形成的?
兴隆与北京平谷区毗邻,两地都是山区,都是著名水果产区,1958年之前,两地都隶属河北。上世纪90年代初两地经济实力相当,而十多年后的今天,却是贫富两重天。
官方统计年鉴显示,1994年时兴隆县农民人均纯收入2901元,而1995年北京包括平谷在内的远郊农民人均纯收入也不过3208元。此后两地差距迅速拉大,2002年时,两地人均纯收入相差3000元上下。而到了2010年,兴隆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130元,与平谷相差8247元。
兴隆GDP与平谷的差距也从2002年的23亿元,扩大到2010年的74亿元。人均GDP从2002年的5000元差距,扩大到2010年的13000元。
在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赵燕霞看来,差距的拉大和行政区划带来的资源分配不平衡有关。平谷被划归首都辖区,北京多年来加大对于平谷的基础投入,使得那里的农业和服务业快速发展。
“比如平谷的大桃,虽然总产量不如兴隆的板栗和山楂,但是有强大的北京市场支持。”赵燕霞解释说,“作为北京郊区,平谷发展休闲旅游和会议基地,水果不仅能在超市销售,还可以通过休闲采摘和旅游,使得水果的附加值增加,这有利于农民增收。”
相比之下,兴隆的山楂、板栗则很难转化为农民的收入。
赵汉全家有5亩地,种了一些板栗、苹果、蔬菜。但因山路难行,这些收成难以卖出去。据他估算,这5亩地实际年收入也就价值五六千元左右。“兴隆的水果没有形成全国性的交易市场,孙杖子村山里的板栗就算运出去,也很难卖掉。”王立国说。
进入新世纪(19.710,0.00,0.00%),作为京津潮河和滦河水源地和生态屏障,兴隆县加入到京津风沙源治理、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等重点项目,关停了一批高耗能、高污染的矿业企业。为保护北京水源地的草地植被,放牧被禁止。种植业也因旨在保护水土生态的退耕还林行动,发展空间进一步压缩。
“孙杖子村全村耕地50多亩,人均山地耕地有1亩多,但政府按要求每户要退耕还林地3亩,实际只有20多亩,”王立国介绍说,“山上还有些荒地,谁去种归谁,但种的意义不大,反正不挣钱。”
“首都经济圈”的公平未来
截至2011年,北京人均GDP达到1.2万美元,接近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与周边贫困地带的反差越来越大。贫富沟壑的消除变得日益紧迫。
赵燕霞认为,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十二五”规划提出的“首都经济圈”蓝图,这一概念借鉴自发达国家。在东京、伦敦的周边都崛起了繁荣的城市群,集聚了全国最大多数人口、最大附加值的产业,以及最大的经济比重。
“过去多年来北京周边的资源更多的是向北京集聚,今后北京要增大溢出效应,疏散一些功能到外围,为周边地区创造发展机会。”赵燕霞说,比如现在北京的文化和高科技等功能在向外疏散,在廊坊就集中起了很多高科技企业。
她认为。像兴隆这样的地方,作为北京周边的生态涵养地区,以牺牲当地经济利益为代价,为北京的环境保护作出了贡献,北京市和国家层面都应该给予这些地方更大的支持和反哺。
这样的思路与决策部门不谋而合。在北京市编制首都经济圈规划的同时,河北省也在编制规划,把兴隆等14个县纳入到一个以北京为中心发展养老、健身、休闲度假、观光旅游、有机蔬菜基地的一个“环首都绿色经济圈”之中。
在工业的发展受到抑制的条件下,兴隆的休闲旅游资源被寄予希望。兴隆在清朝年间曾被划为清东陵“后龙风水”禁地,封禁长达250多年,使得这里风景秀美,气温比京津地区低8℃至10℃左右,拥有雾灵山、六里坪、五指山等尚未开发的景区。
中国社科院旅游中心专家魏小安认为,和休闲旅游结合,兴隆的水果种植业才能注入活力。“兴隆不能叫‘林果立县’,应该叫‘林果引县’,引来游客,那里的柿子就可以从原来5块钱一斤,卖到20块钱一斤。”
当然,这一切首先取决于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能不能先把这路给修好呀?”赵汉全望着村外那片乱石滩发愁地说。那里经过7月21日那场暴雨后,已经辨认不出路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