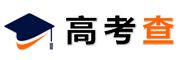罗家伦有一张传世照片。照片里,他着西服领带,戴着圆框眼镜,下巴微微扬起,眼神带有一丝轻蔑。任何凝视这张照片的人,都能感受到一股咄咄逼人的气势。
这股霸气,自“五四旗手”黄袍加身那一刻,便已天成。罗家伦在“五四运动”中声名鹊起,凭的是那份《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宣言短短180字,气势恢宏,结尾两句“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更是传世。倘胸中无热血汹涌,焉能写出如此磅礴名句?更不用说他和另一位旗手傅斯年,是惺惺相惜
的挚友。傅斯年何等火爆脾气?动不动就把宋家、孔家一帮皇亲国戚骂得狗血喷头,人送雅号“傅大炮”。人以群分,罗家伦如何评价傅斯年?“在朋友中,我与傅孟真最亲切!”
罗家伦的霸气,在他1928年执掌清华时更表露无遗。他原本已在北伐军中官拜少将,政治前途一片光明,却经蔡元培举荐转任清华校长。赴任前他与清华学生代表交心,道“来办清华,本系牺牲个人之政治地位,自当以全副精神办理清华”。他不过是个31岁的菜鸟,一到清华,就对一帮老头子痛下杀手。清华原有职员95人,被罗撵走23人;教员55人,竟有37人惨遭解聘,续聘者不过区区18人。
罗家伦撵人,是因那时清华教学水平整体平庸,他铁心要把一流师资搞进清华,不惜开罪一群平庸之辈。此后,他以大手笔延揽数十位学有专长的著名教授,历史学家蒋廷黻,政治学家张奚若、萧公权,哲学家冯友兰,文学家朱自清,化学家张子高,地质学家翁文灏,数学家华罗庚等,均在此期间纳入清华麾下。尤其是蒋廷黻,身为南开大学历史学的台柱子,莫说自己本无去意,南开掌门人张伯苓也不肯放人。罗家伦不讲客套,单刀直入直奔蒋家,说:“蒋先生若是不肯去清华任教,我就只好坐在你家客厅中不走了!”蒋廷黻无可招架,只好点头。
然而倘若你觉得罗家伦只是一介莽夫,那就错了。他心思缜密,毕业后又在北伐军中浸淫,深谙政治游戏规则。他对清华的改造,远非聘请良师那么简单。他真正的目标,是要理顺清华体制。那时的清华,规模不大,居然有三个管家:外交部、教育部、清华董事会,时称“一国三公”,学校办学左右掣肘,长期游离于全国高校体系之外不说,还被外交部安插大量人浮于事的职员。尤其是由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成立的清华基金,更是各方眼中的肥肉。
罗家伦盯准时弊,决心一举破题。1929年4月,清华董事会否决罗家伦提交的学校发展规划和预算,深得蔡元培真传的罗家伦依样画葫芦,学蔡公辞职要挟,就此拉开罗氏在清华最精彩一役的大幕。他先是在各大报刊上公开辞呈,披露清华基金的查账结果,其舞弊、贪污情况,引起朝野震惊。然后他又掐准在清华基金问题上,政府最忌惮的是美国人,便直接向美国驻华公使通报基金实情,提议该基金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代管,主权属于清华,支配权归属教育部,获得美国公使同意,终使清华基金摆脱各方觊觎局面,可以专事服务办学。
而在争取清华摆脱外交部、专辖教育部一事上,罗家伦更是表现出高明的政治智慧。他知道如在行政院会议上讨论此事,教育、外交两部部长均会出席,双方难免一团和气维持现状。他索性绕过行政院,直接将此事提请两部部长均不够格参加的国务会议,并事先征得蒋介石、谭组庵、孙科三位要员同意,最终,清华专辖教育部的议案一举通过。清华办学体制,自此完全理顺。
甩掉一身负担的清华,开始全速奔跑。短短一年,清华连增生物馆、图书馆、气象台、学生宿舍数大建筑,教授前已叙及,课程数目也大幅增加。罗家伦对此也是志得意满,后来谈及这段历史,他自评甚高:“老于人情世故的人,就决不这样做。但我不知道什么顾忌,人家对我的仇恨我不管,我为的是清华的前途,学术的前途。”后来多种复杂因素下,罗家伦被清华师生撵走,没落下什么好名声,但也有声音为罗家伦叫屈,“梅贻琦何以能提出‘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那是因为罗家伦把大楼都修好,他不用操这个心了!”
1932年,罗家伦再次临危受命,担任中央大学校长。当时中国国难当头,亡国灭种已近在眼前。罗家伦认为,作为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对民族和国家应尽到特殊的责任和使命,需要“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以达到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他把自己的硬汉风格注入中央大学,以“诚、朴、雄、伟”四字引领中央大学新学风,尤其是“雄、伟”二字,要一扫民族柔弱萎靡之风,塑造学生的浩然之气。在他治下,1932年还面临被当局勒令解散局面的中央大学,到抗战初期,已成为全国高校无可争议的龙头老大。1938年的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居然有三分之二的考生把中央大学填作第一志愿,足见中央大学声誉之隆。
抗战的烽火,更为罗家伦的校长生涯增添一抹悲壮。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南京岌岌可危,为了延续中国文脉,保留读书的种子,他立即组织中央大学有计划地西迁重庆。中央大学全体师生、眷属,及全部教学科研设备,用船载运,溯江抵达重庆。迁徙到重庆的中央大学,经常遭到敌机的轰炸,在这种不利的办学环境里,罗家伦豪情不减:“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在他的眼里,环境不论怎样恶劣,教育是不能停止的,这同样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存亡。
只可惜,罗家伦因霸气成名,也因霸气所累,得罪人太多。此外,他与国民党高层交往甚密,这样的背景也让他难以摆脱党派斗争的牵累。多方因素下,尽管他为清华、中央大学两校贡献甚巨,但结局都显凄凉。他视傅斯年为挚友,但傅斯年越老越妖,他的人生却是一条缓缓的下坡路,五十岁后即泯然众人矣。然而,为中国留下《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他,注定不会被历史遗忘。